在图书馆的窗口发呆,低头时突然发现墙根长着虎耳草。我是不大喜欢虎耳草的。在《边城》的梦境中,将虎耳草想得太过美好,及到后来真真见到时,很有些失落。
汪曾祺先生纪念沈先生的文字不少,最为人知的应该就是以张充和的挽联为题的那篇《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》。写的很细碎,平平淡淡地记些小事,基本没有评论和抒情,只是记叙。但是很多年来,想起沈先生,首先想到的是虎耳草,然后就是这篇文章中记的一些琐事,比如“耐烦”的口头禅,比如那只后来被杀了做菜煞风景的锦鸡,比如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……
他们都是简单纯粹的人,赤子。我很害怕看到各式各样的悼文或者纪念文字,那些溢美之词往往让人觉得厌倦,所有死去的人都是一样的高尚而出色。
汪老和沈先生名为师生,实为挚友。我向来是喜欢汪老的。他的文字,淡,却有味。他不喜海鲜,说总觉味重。咳,就是这样。中国的语言往往只可意会,确实。有人评价汪老的文字透着一股水意,我喜欢这个说法。安谧的,洁净的,苇子在水上摇曳,疏朗清淡。汪老推崇归有光。从前中学语文学《项脊轩志》,没有好好记下,现在想来,隐隐记得一些散落的片段,也是细碎的一些琐记。汪老写了不少回忆自己家庭的文字,两者文字背后的那种寂寥苍凉的感触,是仿近的。疏放中见凝重,平淡处现奇崛。大体如此。
——庭有楷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
——我年轻时没人说过我像祖母。大概年轻时不像,现在,我老了,像了。
2007年8月3日星期五
订阅:
博文评论 (Atom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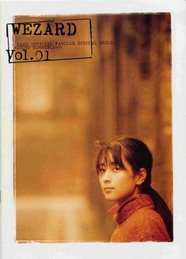


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