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习散记
走下校车,温热的空气扑面而来,霎时间感动得几乎泪流。从未如此感念这座校园。之前汽车刚驶进白城校门,车内就沸腾起来,然后就开始整齐地欢呼。其中不乏矫情的成份,但是,对这座校园的感情,在这个瞬间变得无比的真实而浓烈。我们的灵魂,有一部分深深地扎根于此。汽车驶进校门时,我们突然放松下来,隐隐地,感到了家的气息。
心底其实很乱。短短十几天,似乎漫长得看不到尽头,可是不知不觉中,却很快就走到最后一天。临到登车时,还有些恍惚。车过沙溪,看见对岸密密匝匝的厂房,确实,我在这儿呆了十来天,留下杂乱的记忆。
三化是个很有些破败的企业。现在的国企大多如此。工艺、设备似乎都是遥远的过去遗留下来。一切都属于过去,辉煌与荣耀,记忆与梦想。现今,只有灰暗的破旧厂房与工人同样灰暗的心境。
某个很有人情味的技术员,在给我们介绍流程时说了许多题外话。犀利,尖刻,温暖,慈祥,矛盾在他身上似乎变得合理。企业的年产值大约10亿,他很有些诙谐地称,效益年年降,终于濒于亏损,千万富翁百万富翁,却年年总要产生几位,毕竟,守恒是宇宙间最本质的原则之一。他也很婆妈地说起他与我们同龄的孩子,说起父母对我们的期待,说到动情处声音似乎有些哽咽。后来我没有再见过他。毕竟短短十数天,在一个3000多人的厂子里要见到同一人,还是有些困难的。
我们在控制室坐着。看小说,打瞌睡,侃大山,或者只是单纯地发呆。相隔着一段距离,在房间的另一端,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(蓝领一词果然是这么来的)也坐着,看小说,打瞌睡,侃大山,或者只是单纯的发呆。他们的话题转来转去,始终脱不了孩子房子和票子。高考招生还在如火如荼,同样热火的还有中国的股市。年纪大些的人们大抵都在为孩子而操心,年轻的小伙子们却握着手机低头关注大盘走势。有天,一个看起来有些潦倒的男人,凑到我们身边,问了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,关于学校关于分数关于费用,我们很有些讶异,最后,他很有些忸怩地说了,我儿子刚高考完。我问了他分数,虽然不知道状况但显然让人不能乐观的数字。我们沉默了一阵作思考状,男人安静地离去。我很有些内疚。
一个车间主任。他的笑声洪亮而爽朗,笑起来嘴边的两簇浓黑的胡子会一抖一抖,很有些可爱的样子。他的年岁不小了,在厂子的日子也不短了。他超乎常人的负责与热情,成为我们沉重的负担。往往在控制室里呆得惬意时,他就推开门,用大嗓门吼吼着:走,XX,你带这些个学生哥出去转转,跑跑流程,讲细点。结果往往是相似,他的那些下属,从工段长、技术员到普通工人,都一致消极地回应不会讲。他很有些无奈,朝我们挥手,又吼吼说, 我带你们转一圈去。我们只能很无奈地离开控制室,在高温喧嚣的厂房里设备间穿行。在震耳的机器轰鸣声中看他声嘶力竭地吼着,尽管总是躲在靠后的我基本上听不见他说的内容,可还是充满了由衷的敬意。这是个可敬却不可爱的人。没几天,我们到另一个车间去了,终于不用每天内疚地面对他了。
夜里躲在房里,为着想看的电视节目而争夺遥控器,最终妥协的结果是,美洲杯,亚洲杯,环法,《与恐龙同行》,还有看了又看的《武林外传》。人几乎全是去年在永安实习时的人,分房后见到新的室友,大家都不由得笑了。这个巧合,的确有些妙。看球,不停地塞食物,然后拿某人的绯闻开不断重复却永远也不厌倦的玩笑。每天要送出装得满满的四个垃圾桶,呼~先后有人病了,或轻或重,有缓有急,不像去年永安病得那样诡异而迅猛,没有恐慌,只有一些善意的调侃。涛涛的感冒,伴着发烧,绵延着几乎贯穿整个实习期间;星星的病来得突然而猛烈,可是消得也快,一个下午的点滴就终结了,让某男想以照顾病人为名的跷班计划流产;只有李san的腹痛,居然是结石!很有些诧异。送医院后看见他疼得在病床上翻滚,心中也疼痛起来。陆陆续续涌进病房看望的同学,让同房的其他病人大感诧异。的确,我们在那条冷清的街道上显得别样另类。
登上64米高的造粒塔顶,俯瞰整个厂区和不远的三钢。对面是连绵的群山和柔媚的沙溪。这样的对比很有些怪异。这样丑陋而突兀的工厂,楔入原本和谐的自然间,总让人心里不舒服,而且是这样会让人产生黑色恐慌的破败的工厂。在上世纪50年代前,这个中等城市只是一片青山绿水。在体制内,一声令下,短短几年,这就成为了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工业中心。但是政策调整后,这儿就由辉煌开始没落。将来,这儿会怎样呢?祝福这儿的人们,也祝福这儿的环境,不要再遭到突如其来而没有意义的破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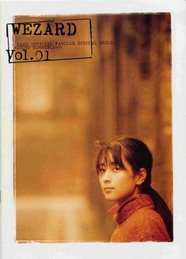


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