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想之十:斩鞍《旅人·白驹》想开
嘿嘿,百文达成纪念……
漫长得似乎看不见尽头的期中考试终于也结束了,很快就是五一长假,突然清闲下来,狂灌水,哈哈……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传说中的分割线---------------------
《白驹》的情节,是青石之战。燮军南下入宛,各方势力,各路人马,在青石这个不大的城外进行拉锯、角逐。最终,青石城破,守军除鹰旗骑军大部和扶风残部撤出,城守、六军、鹰旗步军在鹰旗军留守将领(尚慕舟、阿零、崔罗石等)指挥下与燮军巷战,全部战死。宛州商会向燮军请降。
战役前期,主要是在青石外围展开,双方都在破坏对方的补给线,试图使对方被迫罢兵。这时不得不提起偏马这个小小的城寨。偏马的位置很尴尬,离官道还有两里(这个两里,我觉得很有问题,在军事上,这样的距离可以忽略,应该是二十里之误吧)山路,而且寨子也小,只能容纳区区两千士兵。对南下的二十万燮军来说,完全可以忽视这个小小的山寨,从官道大摇大摆的长驱青石城下。但是,这区区两千人,对燮军的补给线却是一个可怕的威胁,燮军不得不重兵保护辎重。总之,偏马就是一个孤城,刻意楔进燮军软肋的一枚刺,时不时就要扎伤这个巨人。
这样的部署,不得不说巧妙,非常之妙!只要偏马的守军能够长期扎下去,就是一支可怕的奇兵!抢占侧面阵地,无论在防守上还是进攻上,都是极其巧妙的一招。有个印象很深刻的战例,和鹰旗军对偏马的部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中唐安史之乱中,唐军九节度联兵于相州惨败(乾元二年三月),之后,李光弼接掌朔方军,率军防守洛阳、潼关道。九月,史思明大军渡河攻克汴州,直指洛阳。李光弼手头上只有两万人马,防守洛阳几乎是不可能,于是他果断的撤出洛阳,坚壁清野,将军队部署于西面的河阳。河阳城池较小,但是城防坚固,而且背靠黄河,以晋南为依托,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样,史思明就不能放心西进潼关:他的侧翼暴露在李光弼的眼下,一旦贸然西进,遭到李光弼的掩袭,后果就是致命的。
不知道斩鞍写到这段时,想起的是哪个战例。这样的经典战例,大大小小是有许多,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李光弼的这个了,也许是由于战役的悲剧性结局吧。李光弼的部署可算是天衣无缝,可是他还是算漏了还有一个不知兵事只知心急的白痴皇帝:李亨强令李光弼反攻洛阳,邙山一战,唐军再次惨败,潼关道暴露无遗,几乎再一次丢失长安。好的将领,没有好的主帅支持,下场往往很悲剧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传说中的分割线---------------------
既然罗嗦了,就继续罗嗦下去。《白驹》中还有一场不大不小的战斗:燮军设下埋伏,包围了偏马派出的百名斥候。偏马的守军们可以看见自己的弟兄被困的惨状,却不能出击救援:密林里燮军不知布置了多少伏兵,就等着援军踏进圈套。这时青石赶来的鹰旗左路游击,两百重骑,无畏的冲进重围,以惊人的速度和战斗力,撕扯开燮军的防线,让偏马守军得以出击,解救出被围困的斥候。
九州的写手似乎对重骑是情有独钟,几乎都有写到霸气十足的重骑在战场上冲击扭转战局的桥段。青阳虎豹骑,燮军重建的铁浮屠,还有这回的左路游击。
一般印象中西方的骑士的甲胄是极其沉重的,帝国时代中的重装骑士、圣殿骑士,惊人的防护与杀伤力,成为众多玩家的至爱。其实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丝毫不逊色的重骑。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,往往不能算是真正的骑兵,充其量只是骑射手,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,人们一向喜欢称之为铁骑,其实也只是加强版的骑射手(这个在帝国时代II中倒是很客观的体现了,蒙古的特色兵种就是蒙古骑射手)真正的铁骑,还是要到中原来找。曹操的虎豹骑,马超的西凉铁骑,高顺的陷阵营,这些个都是精锐骑兵,但是不清楚是如何模样,怎样战斗。南北朝延续到隋唐,明光甲成为主流。这时的骑兵有了欧洲的重骑的全身防护的模样了(似乎比他们早些,那就算他们模仿我们吧,嘻嘻)
不得不提起李世民。李世民确确实实是个大军事家,大的战略方面不讲,就是临阵的战术思想,也是极其先进的。他是个用骑兵的大家,对骑兵的建设和使用,都有极其高超的技巧。他自己总结说:“每執金鼓,必自指揮。習觀其陣,即知強弱。常以吾弱對其強,以吾強對其弱。敵犯吾弱,追奔不逾百數十步,吾擊其弱,必突過其陣,自背反擊之,無不潰,多用此而制勝,思得其理深也。”他常常亲率玄甲精骑,作为战场上的关键打击力量。玄甲就是精选的一支重骑兵。利用重骑兵的超强防护能力与机动力,实行迂回,掩袭敌军侧翼或后方;或者直接强攻,反复拉扯,只要敌军防线出现一丝缝隙,就可以楔入往复撕扯,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。亚历山大也是用骑兵的高手,他有一支由方阵组成的精锐重步兵,这个就是他的铁砧,然后用骑兵迂回包抄,作为打击力量,将敌人挤压向严阵以待的步兵方阵,这就是西方战史一再强调的huammer and anvil tactics. 还有所谓的坎尼模式,其实也是这个战术的完美演绎。当然,用兵贵在临机。何去非(福建浦城人,我的同乡先贤,作为后学,他的著作当然要读!还有章惇,虽然这个人人品不好,但是还是很有思想和见地的。章楶,他被人记住的只是他的几首词,大抵还都是艳词,但是他出知渭州时指挥平夏之战,击溃三十万夏军,啧啧!同时代的名人大致就是这几个了,杨亿、真德秀都要早或更迟了)在他的《何博士备论》里说,“蓋兵未嘗不出于法,而法未嘗能盡于兵。……法有定論,而兵無常形。……是以古之善為兵者,不以法為守,而以法為用。常能緣法而生法,與夫離法而會法。”这段话是他评论霍去病说的,霍去病拒绝学习古代兵法,强调用兵之道只有依靠实践才能获得,何去非是深深赞同。当然,我也是赞同的,呵呵……
在《白驹》中,左路游击就是作为一直突击力量撕开燮军的防线,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。这样的精锐,有一支就足以自豪一生!大体上军事爱好者都喜欢各式各样的坦克,就是因为坦克扮演的其实就是重骑那样的突击力量的角色,应该都有着骑兵情结吧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传说中的分割线---------------------
拉里拉杂的废话一通,舒畅许多。只是又联想到了张仁愿。谈到朔方军和唐代的军事家,不由得不想起他来。他的名声自然不是很高了,但是在我心中,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战略家。唐朝,我敬佩的军事家,三个,李世民,李靖,然后就是张仁愿。李泌圆滑世故,一不顺就躲起来隐居,而且传说起来就像个老妖精,不喜欢!甚至有人把杜牧也列为军事家,咳咳,写了几篇军事题材的文字,就算是军事家了?
东拉西扯一大堆,懒得写了,以后再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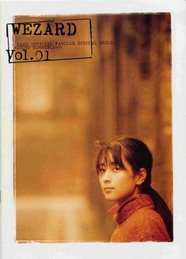


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